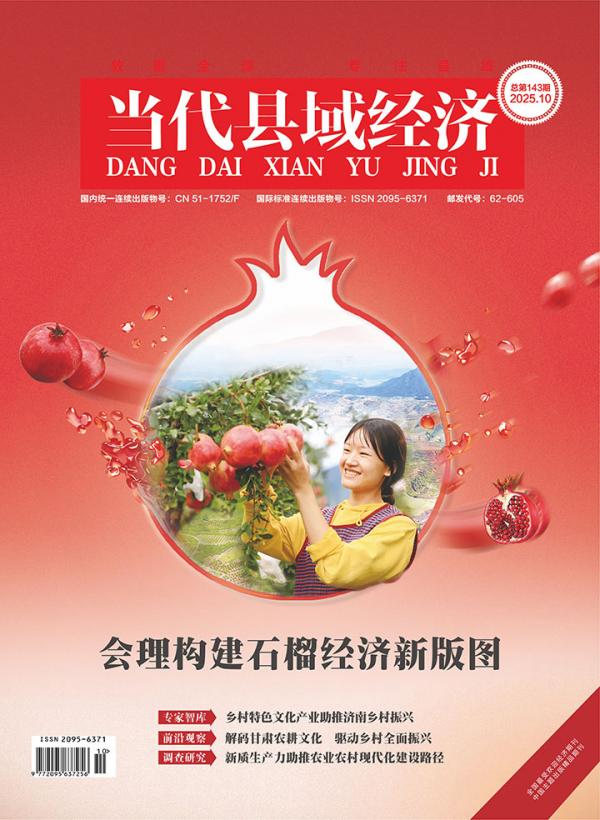
当代县域经济
在线阅读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色,也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和动力。
甘肃位于黄河中上游,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从大地湾文化、周祖农耕文化再到现代丝路寒旱农耕智慧,农耕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历经数千年的漫长演进,承载着丝路文明的深厚底蕴,加之与游牧文化碰撞形成了独特的甘肃农耕文化。丰富多元的农耕文化资源是甘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亟待探索一条“特色引领、文化赋能”的路径,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融入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位于甘肃临潭县的尕湾梁梯田开垦于明代,如今已成为如诗如画的农耕人文景观(资料图)
农耕文化融入乡村
全面振兴的价值意义
农耕文化是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内核。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已接近尾声,乡村振兴即将进入新的阶段,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不再是初期侧重“搞产业、修基建”,实现目标也非单一经济指标增长,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整体提升。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而文化就是乡村的魂,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五大”振兴中实施难度最大,也最具标志性意义。农耕文化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凝聚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中,记录于传统村落、乡土景观间,流传于人文逸事、乡规民俗里。乡村文化的鲜明标签就是农耕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内核和实践抓手亦是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振兴县域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县域作为“城尾乡头”,一头连着城市、一头带着乡村,承担着城乡要素流动的枢纽功能,是承接大中城市产业外溢转移的重要载体。产业兴,经济才能强,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在县域,而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乡村产业发展。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其不仅仅是精神符号,更是驱动县域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从“文化资本”理论看,农耕文化可通过三种形态实现经济转化和产业振兴,包括传统技艺现代赋能、非遗传承人价值兑现的具身化形态,农耕景观文旅开发、农耕文化IP衍生的客观化形态,以及农业文化遗产认证、农业品牌标准打造的制度化形态。在乡村振兴新阶段,农耕文化必将释放更大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农耕文化是重构乡村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在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如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乡村非遗技艺传承主体萎缩,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引发的文化自卑与文化焦虑,西方标准化农业生产经验挤压多样化的传统农耕智慧等。乡村文化自信的消退,深层原因是对自身文化根脉的疏离与怀疑。在这一背景下,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和乡村社会的精神母体,其不能仅仅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逐步淡化并与中国式现代化隔离,而应在新时代加大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及活化利用,实现农耕文化从“历史记忆”到“当代认同”的转变,为乡村社会注入“有根”的自信力,推动形成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文化认同体系。
甘肃农耕文化的独特意蕴
农耕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但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记录,更蕴含着“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甘肃农耕文化秉承了中华农耕文明哲学基因,并由于甘肃“地理阶梯性、文明交汇性、生态脆弱性”的三大特质,在与游牧文化、丝路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淬炼出尚和、坚韧、互愈的独特哲学意蕴,形成了一套甘肃农耕文化精神价值体系。
尚和,多元共生的交融智慧。甘肃农耕文化中的“尚和”,是一种在多民族交汇带和文明碰撞前沿形成的系统性共生智慧,并非只有“和谐”之意。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汉族、藏族、回族、裕固族等民族在此长期共存。农耕民族的精耕细作与游牧民族的畜牧技艺在此相互影响,各民族在文化习俗上相互借鉴形成了各种文化形式,如花儿、社火等,皆是各族人民文化交融创造而来。同时,甘肃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最具代表性的敦煌文化延续近2000年,蕴含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四大文化体系,其与农耕文化结合形成的敦煌农耕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农耕印象。甘肃农耕文化生动阐释了真正的和谐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构建动态平衡的哲思。
坚韧,逆境生长的生命美学。甘肃农耕文化中的“坚韧”,是一种在苦难中孕育希望、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美学。甘肃全域跨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区4个温度带,包括干旱半干旱、湿润半湿润4个干湿区,自然环境多样且脆弱,区内降水稀少,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地带,且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均较严重。因此,甘肃农耕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传承和发展经历了干旱的气候、贫瘠的土地、频繁的自然灾害等重重考验。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认为甘肃旱作区的大部分区域不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但不屈不挠的甘肃人通过艰辛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旱作区农业生产的“奇迹”。目前,甘肃通过旱作农业技术、节水灌溉技术、日光温室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等,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展现了独特的农业智慧和坚韧精神。
互愈,农医同源的互鉴启示。甘肃农耕文化中的“互愈”,生发于农医同根的物质实践之上,在与中医药文化交融中形成“天人互愈”思想启示。甘肃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人文始祖伏羲、“医圣”岐伯、“针灸鼻祖”皇甫谧等历代先贤在陇原大地打开中医药先河,《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仍是指导当代中医药活态传承的实践宝典。农耕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作为甘肃文化体系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哲学理念的共鸣。甘肃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与《黄帝内经》中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相一致,这种“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思想贯穿于农耕生产与中医疗愈的各个环节。同时,农医物种基因库的重叠,种植技术的互通,也体现出发展之道,不在对抗与征服,而在于理解与共生哲学理念。
甘肃农耕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农耕文化传承断层与主体缺失。农耕文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被挤压生存空间,一度沦为落后和保守的代名词,文化建设主体缺失和农民流动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常态。甘肃农村劳动力外流和人口老龄化相较其他省份更为严峻,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农耕文化的根基。青年农民对农耕文化的记忆碎片化、表象化,难以发现其现代价值,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农村地区工作条件和待遇相对较差,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文化从业者,导致乡村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较低。同时,传统农具、古村落建筑缺乏合理保护与现代应用,农耕文化物质载体也存在消逝危机。
农耕文化产业化转化能力不足。农耕文化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撑县域乡村产业发展动力,是当前制约甘肃乡村文化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农耕文化资源挖掘与创新不足,“农文旅”融合发展存在“千村一面”现象,大多停留在民俗表演、观光采摘、民宿体验等显性层面,未能深入提炼其精神价值,本地特有的农耕技术、农耕哲思未得到有效显现。农耕文化系统性数字化转化不足,农业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制约了农耕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与数字化保护。同时,支撑农耕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既懂农业,又懂文化、旅游、市场营销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不足。
农耕文化基础设施与政策支撑薄弱。甘肃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规模较小,推进乡村振兴中“重物质轻文化”较为普遍,更多关注乡村道路、农村电网等生产性、生活性基础设施以及流通性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文化场所、村史馆等人文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财政补贴有限导致传统农耕非遗技术传承利用激励不足。数字基建短板突出,5G互联网普及仍需加强,农耕文化数据采集的碎片化,技术转化的表层化,数字服务的城乡割裂的局面亟待突破。同时,支撑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政策工具单一,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活化利用的政策法规。
甘肃农耕文化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筑牢农耕文化根脉意识重构乡村文化自信。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承载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利用农耕文化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重构,需要在传承延续传统的同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构建与现代文明兼容的价值体系。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保护传统村落与农具、修复古建筑等方式,让农耕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延续。深化甘肃农耕文化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甘肃农耕文化内涵及特殊价值,为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支持。将农耕文化纳入教育体系,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组织实践活动等方式,让中小学生了解和认识农耕文化,培养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之情。开展农耕文化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举办农耕文化讲座和展览,提高公众对农耕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建立完善甘肃非遗传承人名录,实施非遗传承人“师带徒”计划,让更多青年人加入农耕文化传承保护中。
推动农耕文化与县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农耕文化与县域产业深度融合,能够有效破解县域“产业同质化”“文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进一步复兴农产品加工古法技艺,如古法酿造、古法压榨、古法发酵等,为农产品嵌入特色农耕文化基因,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品牌溢价。推进非遗技艺产业化转型,在“农业优先型”县域率先建立非遗工坊,以“甘博文创”为标杆推进“农耕非遗+文创”建设。促进农文旅融合模式提质升级,以甘肃农耕文化为基础,开发具有县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旅游项目,如打造农耕文化主题公园、推出农耕体验游、研学游等。同时,促进农耕文化与中医药文化融合产品开发,以“农文旅+康养”模式讲好甘肃“药生于农、农合于医”农医同源故事。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孵化,成立“陇原农耕产业联盟”,整合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文旅文创企业,对标“甘味”开发“甘农好物”品牌体系,实现农耕文化价值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双赢。
开展农耕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基因库建设。农耕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是以现代化技术应对文化断代的重要举措,对农耕文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进一步强化乡村数字文化宣传教育,依托县域职教中心,开展“数字新农人”培训,让普通农户掌握基础数字工具使用能力,形成百万级数字化生产力储备。用好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培育“新乡贤创作者”,让农民、小镇青年成为“数字农耕文化生产者”“数字农耕文化传播者”。支持“数字乡贤”回流,为返乡科技人才提供创业补贴。组织县乡村干部赴杭州、深圳等数字文化高地开展研修,塑造“数字思维”,实现技术普惠与基层渗透。推动甘肃农耕文化数字化传承保护,对文物、农具、非遗、民俗和古村落建筑等农耕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建立“甘肃数字农耕文化基因库”。进而以数字文化基因库为支撑,推动农耕文化文旅融合,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竞争力。
完善农耕文化政策支撑保障体系。完善农耕文化顶层设计,将甘肃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纳入甘肃“十五五”规划予以高位推动。在甘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相关政策中细化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条款,以县域为单位打造“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样板县”,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农耕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模式。推进农耕文化立法保障,制定《甘肃省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古村落、古灌渠、非遗技艺等文化遗产的“保护红线”与“活化利用”边界。省市县三级制定中长期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行动计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探索发行“农耕文化振兴专项债”,重点支持非遗工坊、乡村文史馆、数字农耕博物馆等建设。以完备精准政策供给为抓手,最终实现甘肃农耕文化从“文博场馆陈列标本”到“乡村全面振兴引擎”的质变。(王惠英 何国莲 丁志鲲 甘肃农业大学;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规划项目《甘肃优秀农耕文化挖掘与传承研究》(2024YB067)]


关注官网微信